



老子认为“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所以人应该容纳别人,能容人 才是真正的善。①武术习练者常要相互切磋,自然滋生出“争强好胜”的心 理,然而传统武术无论是门派内部还是跨拳种之间的比试都强调“点到为 止”,轻易出手伤人不仅难以在武术界中树立自己的威望,甚至会引来前辈指 责,成为行内不受欢迎的人。许多门派创始人或重要代表人物,如陈式太极 拳陈发科、杨氏太极拳创始人杨露禅、大成拳创始人王多斋在不得已进行比 武的情况下尽量保全对方的颜面,要让对方感到技艺上的差异而外人甚至丝 毫未能察觉胜负已分。对于习武者来说,克制自己的“好胜心”是非常困难 的,大多数习武者正是为了“战胜对方”而开始习武道路,逐渐在师父和师兄弟的引导下强调“争而不伤”,最后运用“不战而胜”的方式(展现功力、打套 路)决出胜负。
道家所讲的.'谦让不争”并不是说要成为“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任人宰割 的被动者,老子思想的精髓是让人克制对客观世界不必要的物质名利的追 求,达到人人“自足者富”的境界,不会为一己私欲而增添对他人和社会的危 害。①虽然武术练习强调的是人与人格斗的技术,但在练习或交流过程中不 能为了追求“击打对方”而不择手段,“撅土扬沙”式的偷袭暗算都是被人看不 起的伎俩,不能“争斗心”过强。老子所言的“不争”是指用平常心对待比试的 胜负,追求的是“天之道,不争而善胜”的最终境界。此外,任何时代的习武者 都活在一定社会关系之中,往往一次比武切磋的输赢造成日后关系恶化甚至 导致几代人“结怨”,因而分出胜负又不伤及颜面的结局往往能促使双方成为 武学,,挚友”,正应了老子所说的,,持左契而不责于人,,。咏春拳门内技艺切磋 并不是戴上拳套打倒对方获得胜利,而是两者双手贴在一起内翻外转进行攻 防技术的对决,这种“藕手”练习(类似于太极推手的方法)不仅能分出输赢, 也让对方不受伤,这体现出咏春拳在比武切磋中注重人际关系的协调,注重 不争压倒式、侵略性的胜利。这种技艺的较量不过是检验武术技术的方法, 因而更能让咏春拳在不同人群中广泛传播。
“处雌若水”思想促生武术“贵柔”风格
先秦思想家常运用“水”来思考,如《告子上》中“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 也”,《宥坐》中的“大遍与诸生而无为也,似德”。但是老子更系统地阐释了 “水”与道之间的关系,用水这种“处下而不争”的性质来阐释“道”
讲究的“人之道,为而不争”,恰是八卦掌旋转身形避开对方正面进攻从侧面 还击精妙技击策略的思想依据,太极拳习练者长年不断相互推手,寻找的正 是对方进攻力点的变化时机.力求放松自己的强硬身体和过于激进的心理状 态,达到“随屈就伸”和“不丢不顶”的绝佳境界。当然在传统武术131个拳种 中,并不是所有的拳种都提倡“柔弱胜刚强”的技击思想,即使是讲究“硬打硬 上无遮拦”的形意拳和八极拳同样还有“避实击虚”“声东击西”的技击 战术。①
老子所提倡的“处雌”和“若水”是用来寻找事物转换趋势的临界点,在远 没有形成明显态势的时候占据有利位置,这就是“弱者,道之用”的本意。② 传统武术认为对方“老力已过,新力未生”的瞬间是反击的最佳时机,当然要 想抓住这一转瞬即逝的机会,没有超强的洞察力和反应力是难以实现的,所 以太极拳推手、形意拳搓手、咏春拳擒手都在敌我手臂接触情况下形成两力 平衡,成千上万次练习即为了抓住破坏这一平衡的微小“先兆”。可以说,武 术招式千变万化,不可能学完,但万变不离其宗的是,训练自己劲力变化和捕 捉对方劲力转换的能力。这是传统武术共同追求的目标,只是不同流派实现 途径不同,解读方式不同而已。
老子思想中的“知雄处雌”“不争而胜”等观点,正是处于弱势地位的人在 周围环境中自我保护的手段,最终达到“无为而为”的目的。③这位具有高超 智慧的古代先哲为中国武术技击观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换言之,运用老 子思想能更加清晰地透析出中国武术本身重重矛盾背后的真相:武术来源于 搏斗,其技击性一直存在,但是受到传统道家思想及社会规范的影响,人们已 经关注技击的“体悟”过程,这就是解开“武术指向技击的同时又回避技击”问题的关键。正因为受到“无为而为”思想的影响,原本不断追求击打效果的传 统武术更多地追逐“来留去送”“粘连随”“攻守同期”等精妙技法,正如一位民 间拳师所言,中国武术是一种“琢磨”人的事。从上述老子思想对武术技击观 的影响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出,长期以来的把道家思想视为消极思想的观点不 科学。
传统技击性的准确定位
普通大众在评价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武术时,常用“可不可用”或 “能不能打”等字眼.学界对武术技击性的界定也一直存有争议,因而理清武 术技击性已经成为影响武术未来发展的重要问题。一部分学者认为应忽略 武术技击性,以求得武术更加宽广的发展空间;而另一部分学者坚持将武术 技击性作为武术的本质属性进行维护,认为失去“技击性”的武术将变为没有 灵魂的“舞蹈”。武术是“指向技击同时又回避技击”的自我矛盾体,还是技击 在武术发展中逐渐被消减甚至在今后可以被取代?
从历史发展脉络看,在元代之前,中国武术是以擂台比试的形式进行技 术交流的。民国武术家赵道新曾提出,明清形成的流派武术正是“擂台中心" 消失后武术技术纵深发展的结果。不同流派对武术技法有着不同理解,从而 形成了风格迥异的技术特征以及以此为基础建立的武术理论体系,而经历这 一重要转折期的武术技击性也已悄然变化。由于武术技击功能的广泛影响, 技击性成为武术区别于其他体育项目的最主要特征。但从完全追求技击效 果来看,武术呈现出“满遍花草”的繁杂也广为人们诟病,回避技击性的武术 被指责为“没有灵魂的身体舞蹈”,技击性俨然成为武术手脚上的桎梏。武术 界以“喂招”和“讲拳”来拆解武术动作最终难以证明武术格斗在现实中的“实 用性”。媒体为了凸显传统武术技击特点而特设比赛规则的《武林大会》和 《武林风》,擂台上选手不尽如人意的表现再一次让充满武侠想象的普通大众 难以接受,导致讲究“打练结合”的传统武术的技击性再次遭受质疑。长期无 法准确地对传统武术技击性进行界定,影响了人们对武术的喜欢程度,也导 致部分研究者对武术产生偏颇的看法,甚至影响未来武术竞赛与传播途径的 选择,因而从学理上对武术技击性进行界定已是迫在眉睫的事。
武术技击性讨论应仅限于传统武术
学界对传统武术与现代武术、民间武术与官方武术、竞技武术与大众武 术这三对概念的使用仍不规范,很多研究将本该限定在民间武术范围内进行 讨论的问题放在“武术”范围内讨论,本该称作“竞技武术”的也统称为“武 术”,在此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就存在问题。另外,长期将传统武术与竞技武术 作为武术两大组成部分,这种逻辑上并不周全的分类方法产生的危害并未能 得到足够重视,这种“约定俗成”导致武术界将传统武术对应于竞技武术,实 则传统武术是相对于现代武术而言,而现代武术除了广为人知的竞技武术 夕卜,也包括民间创编的新拳种及各种流派武术的新形式。
我们常说的,'武术”范围很广,包括竞技武术、传统武术、健身武术、艺术 武术等在内的所有武术样式。虽然长期以来“武术”多指传统武术,但是武术 的审美、健身、娱乐功能不断被大众所认识,武术种类也随之丰富起来。由于 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位,谈论武术技击性的命题从逻辑上讲也就不能成立。自 2000年之后,学界大量关于武术本质、武术技击属性的论文大多是直接围绕 武术的技击性进行讨论,由于停留在对“是”与“非”的直接判断上,缺乏将武 术不同内容区分开来进行判别的思路,所以得到的结论可信度自然不高,在 此基础上提出的武术发展策略也就存在“以偏概全”的不足。另外,竞技武术 不适合讨论技击性。学界还有部分学者对现代竞技武术的技击性进行探讨, 显然忽略了竞技武术(套路)本质为体育项目的事实,不论选手在比赛场上竞 争得如何激烈,这都是在已经脱离动作实用环境下进行的胜负之争。正如我 们不会也不应该谈论击剑或古典式摔跤运动项目的实用性一样,包括散打在内,讨论任何一项体育项目的技击性本身都存在逻辑上的错误。回首竞技武 术发展初期,其曾受到“技击性”判断的严重影响,20世纪50年代展开过一 场对“唯技击论”的批判,让竞技武术的体育功能与价值重新回到了重要位 置。可见,只有传统武术才能进行技击性判断,而且传统武术拳种流派繁多, 所包含的技击性程度也并非是均质化分布,如以单式动作(类似于散打、巴西 柔术、泰拳基本技术动作)为主的心意六合拳、意拳(后更名为大成拳)的训练 方法更加接近技击格斗现实。限于单个拳种的技击性判断则更是一个复杂 而细致的研究领域,本书只讨论以套路为主的占大多数的传统武术技击性界 定所面临的问题。
传统武术技击性的准确定位
统武术具有技击性但并非以“技击”为目标
学界关于“武术来源于原始社会阶段人与兽斗,人与人斗”,“技击是武术 的本质特征”的言论正是对武术技击性的一种肯定。①但是大多数人在思考 武术与技击之间的关系时,并未对技击的概念进行清晰分析,学者多用“武术 技击性”或“武术的技击属性”来表述,显然武术与技击并不同,技击性是指武 术动作所具有的实战运用功能。我们可以先从“技击”这一概念入手。“技 击”一词最早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如“齐人之技击不可遇魏惠之武卒”,“齐 人隆技击”(《荀子•议兵》).“齐憨以技击强,魏惠以武卒备,秦昭以锐士胜” (《汉书•刑法志》)。技击最开始是指上阵杀敌的士兵,《辞海》的解释是“战 国时期齐国经过考选和训练的步兵”。②而《辞源》将技击解释为“击刺之事、身体活动能力,“敢于凭借杀敌的意志和敏捷的身体活动能力,上阵 打仗,杀敌,就叫作技击”。由此可见,“技击”一词中所有“技术”的施展都是 为了达到“击杀”这一最终也是唯一的目的。传统武术是以击打或控制关节 等手段与对手进行练习的格斗技术的,具有高深功力且有武德是习武者所渴 望的目标。
单从上述技术特点这一角度分析并不能将传统武术的技击性表述清楚, 正如戴国斌指出的“武术指向技击但又回避技击"这一看似非常矛盾的观点, 传统武术长期受到中国伦理道德及社会规范的影响,已经从毫不留情击败对 手的技击层面发展到追求“不战而胜”或“点到为止”的与对手和平解决冲突 的层面。习武者不能简单地运用暴力解决问题转而寻求一种能让自己融入 周围人群并得到大众所接受的生存方式.从而也就不愿争强好斗.也就不想 惹是生非。民间千年不衰的“关帝崇拜”现象存在的原因在于关羽义薄云天 而不单纯因为他功夫过人,如果依照欧洲人对于古老维京人的折服和对蒙古 铁骑的态度,给予获得胜利的强者最高的崇拜与敬意,那么,获此殊荣的应该 是武功最高强者,如三国时的吕布。民间武术谚语有“没有千里的威风,但有 千里的朋友”,“行走江湖”没有过硬的武功不能立足,但没有朋友“帮忙”也将 会寸步难行。的确,打败对手可以为自己赢得名声,但是处处树敌则会让自 己陷入不停争斗的“漩涡”.所以传统武术界有很多和平的比武方式.甚至有 两人水平高低彼此心知肚明而旁人看不出胜负的“比武”事例。
传统武术追求自我修炼的“功夫”层次,技击只是达到目标的手段
传统武术并不提倡“致残致伤”的击杀技术,反而有“十打十不打”“八不 教”这样的禁忌。传统武术中大量的打拿结合、快摔制敌、关节控制的技术都 是在降低伤害程度的前提下运用,甚至为了保护对方身体安全还创造出太极 拳的推手、形意拳的搓手、咏春拳的藕手这些不伤害对方的功夫套路,更有甚 者利用不接触的劈砖分石、扬枪刺物、飞镖入墙这样的功夫显示来一较高下。 受长期的中国传统礼仪及“和”文化的影响,原本血腥暴力的技击性手段已经 烙上道德规范的痕迹,武术不再是追求“击必中,中必摧”的击杀术,而是作为 社会关系中习武者自我保护的一种“生存之道”。在进一步揭示传统武术的 真正目的之前,我们不妨进行一次这样的推理:第一,从击杀对手效果(造成 对方的损伤程度)来看,徒手不及器械,手持器械不如远射弓弩,弓弩不抵枪 械,而这正是军队提升作战能力的发展历程,也是枪械取代冷兵器及兵器研 发朝更远程、更具杀伤力的方向不断发展的佐证;第二,从获得技击能力的时 间成本上看,徒手搏斗技术长于手持兵器,手持兵器技法长于弓弩,而弓弩技 法要长于枪械。所以,在最短时间内能掌握且具有强大杀伤力的工具首选是 枪械,而非需要更多身体训练技能及要求如此精细的武术。
由于民间武术技法“繁华绚丽”,开始偏离“击杀”目的而恣意蓬勃生长, 甚至影响军事领域中实用技击的地位。著名军事家戚继光曾著书提醒军中 官兵,防范这种“花式武艺”在军中蔓延,“凡武艺,不是答应官府的公事,是你 来当兵,防身立功,杀贼救命,本身上贴骨的勾当尔。武艺高,决杀了贼,贼如 何又会杀你?你武艺不如他,也决杀了你。若不学武艺,是不要性命的呆 子”。①在简单实用的传统武术技击技术上滋生且蔓延开来的“花法”,与击 杀对方的军事目标背道而驰,却形成了传统武术所追求的闪展腾挪的身段、 盘旋急转的步法、粘连相随的技巧,技法虽然精致细腻以至于实用范围受到 限制,但成为千万习武者穷其一生追求的目标,而这正是所有武术文化及伦 理道德得以附着的关键点。从文化的三层论来看,技术虽处于最外层,却也 是武术内核部分制度(武德与戒条)、文化形成的基础。只有以习练武术、获 得功夫为目标的传统武术,才能衍生出独特的武术伦理与文化,使传统武术 在经历漫长历史选择与洗涤后,在当下社会环境急剧变化的情况下,其文化 层面得以保存。
传统武术注重“打练养”三位一体,技击性只是其中一个特征
武术执行着不同于技击的标准,受二元到多元的开放思维影响,使得“看 似并不复杂的搏击技术”最终发展成为技法丰富的中国武术技术体系。①中 国拳法具有集看、练、用多种功能为一体的特点,而这一特点不仅是我们解读 和理解武术技术的一个认识基础,也是真正认识武术文化的一个不可忽视的 前提。值得一提的是,从武术发展的历史看,技击与武术之间的相互影响从 来就没有终止,有军事用途的技击术流入传统武术体系,也有传统武术技术 经整理进入军事技击训练体系。十分有趣的是,我们只是人为地将传统武术 (民间武术)和军事技击分开,实质上两者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技术屏障,两 者最终形成了风格迥异的技术,主要原因是各自目的不同。传统武术涵盖了 看(观赏)、练(自我完善)、用(技击实用)等多种目的,且“用”是被很多条件限 制的;而军事技击追求的目的就是实用,用最快的速度制服或消灭对手。传 统武术门派拳种的不断发展,各自理论和技法不断完善,形成了完全与技击 相异的评价标准。如果传统武术使用技击的“击必中,中必摧”标准,那么其 会从“枝繁叶茂”变为“简约直白”的击杀术,不会逐步发展成为集“打、练、养” 于一体,融合格斗、运动、养身等多种功能的武术体系,消除所有关于技击的 想象空间,则不会有充满乌托邦色彩的武术套路的发展。②邱丕相教授认为 传统武术套路的目标不是制胜,不是“一拳打死牛”(技击),而是身法自然的 整体协调,如果是为了技击的话,套路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与余地。
讨论传统武术技击性应设立的限定条件
各家有各法:传统武术技击性以各流派技法标准为前提
传统武术技击性衡量使用不同的标准,各流派之间执行的技术标准不 同,如形意拳有自站桩、行拳、递手、实战一整套的详细技术要求与规定,但将 它放到太极拳、八卦拳、洪拳、咏春拳体系中则不适用,而且还有相互矛盾之 处。即便是相似的拳谚.如咏春拳的“守中用中”、形意拳的“洞出洞入",在表 达方式和动作外形上看起来相似,但动作用意和实战运用思路完全不同。从 总体上看,传统武术的技术检验更多地发生在门派内部.因为相对而言用相 同的标准评判出来的胜负更加公平,即便是发生在门派之间的比武,也不会 因一时胜负致使一个门派自此消失于“武林传统武术形成的是百家齐放 的发展势头,由于各自封闭的技术体系,没有任何一个门派可以通过比武“一 统天下”,究其根本原因正是各家有各法,各自标准不同。
中国式浪漫和技击“乌托邦"理想融入传统武术,传统文化及审美情趣都 找到合适的栖息场所,对传统武术进行“人化”改造,体现出中国智慧。无视 武术与技击的分离,造成大众对武术存在过高的期待和过于完美的想象,混 杂着武侠与想象、武术与传说的想法给传统武术笼罩上一层层神秘面纱,累 积迭加成大众想象中的“武术\ 1987年,武术界发现竞技武术套路过于强 调动作难度而忽略技击表现,曾经提出将套路和散打合并为一项综合运动项 目的设想。30多年后,这样的设想并未能成为现实,套路和散打由于竞赛规 则、运动员选材、训练方法和思路完全不同,完全是两种具有不同性质的项 目。传统武术看似“打练结合”的综合运动,然而,传统武术的“打”只存在于 各自流派技击标准下的技击,如果将流派武术技术“屏障”去除,我们所能看 到的众多“花式”将难以发挥其个性,最终成为简单而一致的技术,这正是赵 道新所说的,“擂台”验证技艺的标准消失后.流派武术才得以繁荣和发展,因
而吴式太极的“斜中寓正”在杨氏太极的“正中”技术标准下就不算规范,而咏 春拳的双膝内扣的“二字钳羊马”也不会符合形意拳的“手与脚合、肘与膝合、 肩与胯合”的标准。传统武术技击性讨论的首先就是要建立流派武术各自的 技击标准,任何试图“统一”传统武术技击标准的举动都是毁灭流传至今弥足 珍贵的“原生态”武术样式.传统武术自我传播能力欠缺,如今还受到武术“技 击性”判断误导,所以及时理清传统武术技击性问题具有更加重大的现实 意义。
“能击”还要“善舞”:传统武术技击性负载艺术审美功能
蔡龙云提出,武术既有实用的价值,又对身体的健康有很大的帮助,而且 在表演上也具有高度的艺术性。①传统武术至少具有技击、健身、审美三种 功能,传统武术有少林易筋经、形意站桩法、太极养生功等具有明显健身功能 的内容,正所谓“武医不分家”,很多民间武术拳师也会治疗跌打损伤或掌握 了特殊功效的中药方(万籁声所著的《武术正宗》中就公布了自然门药方),同 时健身性并未对传统武术技击性造成限定。“颠倒生物钟”的子午功法及其 主要内容为拍打和憋气的硬气功、借助于电流的训练方式对身体产生影响等 都有待运用科学方式进行更合理、客观的解释。无论在训练方式还是在动作 编排上,对习练者身体健康的要求并未能限制传统武术技击性的发展,同时, 艺术审美却成为附加在技击性之上的限定条件,在传统武术技术发展过程中 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早在明代,“花式武艺”已经流行于民间,甚至在军营中也颇具影响,时任 海防重要军事将领的戚继光曾告诫部下“舞对(击)二事全然不通”,极力抵制 没有实用价值的“花式武艺气自宋代就开始流传的“套子武艺”武术形式被 认为“图取欢于人”的表演,演练者自身对艺术审美的追求,翻腾跳跃只为体 现足够敏捷的身形,静定动速的变化只是充满技击想象的。可见,武术套路展的主要动力。翻开传统武术拳谱不难 发现,众多拳种创拳初期往往只有数个套路,如心意六合拳最初只有四把捶, 但后来发展到形意拳已经有五形连环拳、杂势拳、劈拳、龙形八势、燕形、熊 形、行式连环拳、连环八势、保卫拳、十二混捶,更是衍生出太极形意、形意八 卦各种套路,几代传人传承下来则衍生发展出多种套路.武术套路数量成倍 增加,而这一不断追求创新和催生不同“作品”的特性与艺术创作有着惊人的 相似之处,简直可以说武术拳种是一代代民间武术家关于,'技击”的一部部艺 术作品。
武术套路体现着传统武术的审美取向,其中对练是对技击格斗现实的 “模拟”,所有的动作都遵循“点到为止”的原则,技击时需要的随机而变已经 转变为事前确定好攻防双方的“预排”;单练则直接让现实存在的对手“消失” 进而完成一个人的“武舞”。一位民间拳师曾总结道,“中国武术搏斗技术,说 白了就是琢磨人的玩意儿”①,体现出传统武术注重技法的丰富和巧妙,关注 的是对技法运用的揣摩与想象。所以“善舞”成为以套路为主的传统武术无 法回避的重要前提。因为“套路是管窥技击的窗口”,是关于技击进行无所不 能美学创作的示范。②在戴国斌看来,武术套路存在这样的悖论:“既是技击 的现实,又有技击的乌托邦。”这正是传统武术技击性受到艺术审美限定的体 现,在传统武术的技术体系中,“能击善舞”是相互融合、彼此影响的两个因 素。至此,长期困扰学界的“武术指向技击同时又回避技击”的难题也就迎刃 而解了。
将技击性判断用于竞技武术或扩散到整个武术范畴内谈论都会带来误 导和混乱,只有传统武术才适合进行技击性讨论,传统武术技击性并不能成 为终极目标,其只是“打练养”三属性之一,并且受到流派技术标准和艺术审 美的限制。中国传统武术的繁荣与发展正源于武术流派对武术技击性的不 同看法与理解,这种近似于艺术创作的方式将技击、表演和养生进行深层次 的结合,“打练养”已经成为不可拆解的整体,同时击杀对方使之致残致伤的 技击术受到社会伦理和人际关系的影响而演变为一种自我修炼方式,因而武 术技击性受到艺术审美、流派技术标准的限定。如果我们不管传统武术的发 展历史和技击性内在逻辑,以追求“击必中,中必摧”简单的技击目标来推动 传统武术竞赛的发展,这种做法只是在重复民国时期国术比赛或散打试点阶 段的探索,结果只会有两种情况:一是僵化的流派技术规则让武术技术特征 无法显现;二是破除技术限定,使开放式的比赛变为散打或近似技击的运动。
武术套路是人们最为熟悉的武术形式,但对其定位一直存有争议,它是 通向技击之路,还是用于表现技击之“舞”? 20世纪的“武舞之争”虽已淡去, 可是武术的技击属性长期束缚着中国武术套路迈向艺术的脚步,导致武术套 路仍不能与中国书法、京剧、民族舞蹈一样被视为“艺术”进行传承与创新。 如果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对面临中断的武术技艺进行的及时抢救,那么 理清中国武术套路的技击与艺术之间的关系,给予武术套路源源不断的艺术 创新动力,才会使其发生根本性变化。近年来,武术套路艺术化研究成果虽 不断涌现,可大多关注的是武术“美”的验证,仍未涉及武术套路审美中技击 与艺术的关系判断。笔者从武舞同源、武术套路的审美境界以及对技击的超 越这三方面入手,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中国古代的舞蹈大体可分为文舞和武舞两种,文舞执羽翟,武舞执干 戚。①《山海经》中关于刑天与天帝的争斗,“帝断其头,葬之常羊之山。
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郭璞注,干,盾。戚,斧也),①是最早的关于 武舞的记载。《韩非子•五蠢》中“当舜之时,有苗不服……(舜)执干戚,有苗 乃服”,持干戚舞具有“战争之神生生不息、顽强抗争的精神表征”,②逐渐形 成了“敬天祀祖、娱神降神、象征兴亡的重要宗庙军事体育舞蹈形式”,可见中 国原始武艺和舞蹈具有相同的起源。③楚汉之争时“项庄舞剑”反映出这种 持剑做技击动作的表演已经在军旅中存在。“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 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霍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彩龙翔。 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唐代 杜甫不是描写公孙氏超乎常人的技击搏杀能力,而是表现其舞动剑器给人以 美的享受和震惊,观赏者与演练者产生共鸣。“剑舞若游电.随风萦日回”(颜 真卿《赠裴将军》),裴旻将军的剑术表演和李白的诗、张旭的字并称为“三 绝”。④唐代持剑自娱或在人前表演已经是常见的活动.“三杯拂剑舞秋月, 偶然高咏涕泗涟”是自娱;“起舞拂长剑,四座皆扬眉”则是表演(李白诗)。宋 代“瓦舍”中的武舞表演已经具有职业化特征。这些都是古人将技击与艺术 相结合的表现。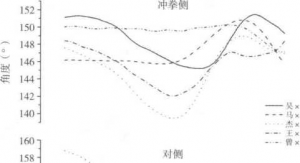

浏览966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