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3月25日至27日,我应邀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2013全 国老子文化机构联谊会”(会后发表了《北京宣言》)。赴京期间,我顺 便拜访了作家、学者和武术家的刘俊骤先生(他是“东方人体文化学” 的创立者)。多年不见,交谈甚欢。临别时,他将大作《武术文化与修 身》(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赠送给我,回昌后翻阅一遍,获益良 多。
(1)
刘俊嚷先生在书中说,20世纪的武学大师王苔斋先生通过自己40 年习拳体悟把站桩研究至深,成为他创立意拳——大成拳的基本内容。 王普斋创立的大成拳负载着丰厚的国学内涵,他的《拳道中枢》总纲, 把国学原典《内经》《中庸》的精华,以站桩去体悟,这一点至今没有 引起重视。
王普斋先生的总纲开篇和结尾都紧扣国学要义:“拳本服膺” 一语 点出武术修身之根本。“服膺”者,谨记在心、衷心信服之义。语出 《中庸》九章孔子对颜回的赞语:“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 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王苓斋先生在《拳道中枢》总纲最后一节更明确指出:“信义仁勇, 悉在其中,拳拳服膺,是谓之拳。”再次引用《中庸》之语,再三阐释 其武学思想源自中华国学的特点。
在《拳道中枢》第五段直接引用《内经》“上古天真论”,对于这 段话,千百年来常常被人视为神话,不求实解。正是王釜斋先生用大 成拳站桩的功夫做出的史无先例的实解。
《黄帝内经》是国学通典,南怀瑾先生等智者早就指出它不单纯是 医学经典,而是修身治国的通典。但对它的许多深刻的东方人体文化 学的精义,却始终未被学者们参透,这段原文如下:“黄帝曰:’余闻上 古有真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故能寿蔽 天地,无有终时,此其道生。“提挈天地”并不是把天举起,把地 提起来,而是形容锻炼达到最高水平者的伟大气概和昂首云天的想象, 亦是一种桩功的意念活动。“把握阴阳”则是指站桩时掌握阴阳虚实的 规律。“呼吸精气”就是“吐故纳新”在空气清新的环境站桩。“独立 守神,肌肉若一”是古代真人修炼身心的一种方法,是站桩的最早记 载。
大成拳学家这种体悟认识,无疑是深刻的。
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武术家为强种强国砥砺身心,探源 索隐,对武学进行了深入研究,在道器双馨的中华元文化的指导下, 内家拳法形意、太极、八卦都在20世纪初叶,出现了一些大师级的人 物。
出身于形意拳门的王普斋,在其溯源探本、身体力行中,创造了 意拳——大成拳法。这种以“站桩求物”为主、完全扬弃了传统武术 套路运动的拳法,表面上看好像与艺术没有关系,但实际上大成拳却 是真正找到武舞同源、双璧共辉的根本。
王苔斋先生经常表演“健舞”,从20世纪20年代,直到他临终前 一年,1962年在保定召开的河北气功学术会上,他表演了 “健舞”和 “勒马听风舞”可为一证。
王苔斋先生在《拳道中枢》总纲第九章中所说:“离开己身,无物 可求;执着己身,永无是处。”他把“物”具体分为“身内与身外”, 而根本就是中华国学各家皆重的“道”……
前不久,我在王苔斋先生未曾公开发表的《拳经述径》一文中看 到其言:
“拳学之道广包寰宇,含容万物。大合于天地,小系于毫厘。共生 死攸关,及寿之长短。故当视以大道,切勿轻之矣。
胸怀顾家国之忧,行止关利民之志,正性情之偏斜,悟人生之极 理。
意境当高远而求索,清念节欲以尽善为,近人当平凡易处,处世 必练达谦和。
虽理有借于佛、道、儒、医,但莫迷信于牵强受制,故拳学之道 为独立之一家也。
言独立者是拳学为专门学术也,非是佛、非是道、非是儒、亦非 医也。
另,诸人多重术而求拳功,余独重理而求意,非余只重于理、意, 但无理念、无意境,其拳之内涵、韵味、精神、意感皆失,单于形、 力、术、法中求之,终非大器之学,是迷径也!
理、意合于神、意,神、意系及形、力,道正途明,自无失而必 有得也。
故理、性为上等之行,因、果为中乘之径,万物一理,违理者所 求皆非也。
拳学首重养生,是先保生命,健身强体也,无病方为健,体和心 自和,由此渐入练,功效自与日增。
功得方可用,方可言技击,自可练技击也。
所言次序先后之途径不可倒置,否则为戕生入误途也。
途径不得,无从入手。简者不知,莫求繁深,小者不明,难通大 意。
当具理而行,具意而为。意指宗旨,亦为神、意。
松、静为本源之基,紧、动为随源达变。
争为两向互为,整体为通身一气。缓求速至,慢中得快。神决胜 念,意导于形。关连为重,过犹不及。
似有若无,不期而至。若心念不定者法要难求也。
余之拳,诸功各有其长,互有相关,而互不可代替也。
果掌握诸功之后,反又似无,其理不难通也,在有意无意间作, 自能统之为一,实本能生也,不思自至。
水满则溢,月圆则缺,不可过,亦不可不到,火候也。
肌松如绵似水者,是练精之果,肌亦可坚硬如钢,此是真精。
如达此内质之变者,方为真效,形表之变而不及也。
入门径后方明此理。非指入求师之门,是言境界之门也。体认、 悟修并具者,方入正轨之径;身心合一,即窥上乘之选。
式不在多练,功应求多知,是选练之法要也。
神、意真,形、力自至。养、练、用可同修,偏废为误也。
道、径若明,参理修功,悟后则通。
心和、气平、性定、身静、体松为健身之途,强体之法,万勿违 之。
而善、慎、仁、勇、德、智兼备是求意境之源,合神会意,自内 修求,与外界合意,则妙趣横生,任为而做,内韵含精。
此时之境可不拘于形式也,有形至无形,有意达无意,是入层次、 上境界之途也。
强求不达,不期而至,不可急躁,亦不可懈怠也。
抽象中可悟出实象,神意中可求其功效,此非狂谎之言词,实拳 学之奥理,众人不知,余自独得也。
门中之人亦应慎心求之,自可明辨,自可得之。
世无坦途,遇难当坚、逢困求解;轻而易得之事,无功受禄之人, 世间鲜有也。
旧时习拳有’过关’之说,余之拳亦有比若’关’者,半时之桩 可为静功第一关;一时之桩可为二关;二时之桩可比三关;有人之桩 只站数分钟,下步功法永无训练之条件也,即练也是无功之为。
所以有半途而废者,有半知半解者,有平庸失败者,有悟求功深 者。
拳不光在学,而更重于练,练应重于勤、坚。
功效在于领悟,出众在于心谦,境高多为深隐,所以深藏不露者, 久必为大器也。
虚张声势,过市招摇,贬人抬己者,均因心狂气躁,非大家之器 也,此辈多意境低庸,常有败绩也,害群之马就指是辈而言。
总之具德为首,具道则明,知途不迷,得径(义理)辨境,拳中 无愚人,老诚非指愚,老诚者、憨厚者、谦慎者、深隐者、敬人者皆 为极聪明之人士也。
自作小聪明,将他人看成愚人,骗他人者是真愚也,久必自害也, 永无成。
求拳勿只专求于技、于术、于功,当先求德,先于仁、善、义、 慎、敬中求之,日后成大道可也。
少练,壮练,老更练。
功无长幼,各辈同参。修研至耄,颐养天年。
平易待人,敬结善缘。得登高境。人更逊谦。拳之经典,述径持 环。切记切为,拳道无边。众皆重道,吾道得延。后人承继,吾拳有 传。”
举凡看过苓斋先生此文者,皆叹曰:拳学之精论也!国学之根本 也!
(2)
王苔斋先生曾说:“若从迹象比,老庄与佛释,大李王维画,玄妙 颇相似,班马古文章,右军钟张字,造诣何能尔,善养吾浩气,总之 尽抽象,精神须切实。”
平时,苓斋先生对弟子们的风度和仪表要求是“举止应恭谨,如 同会大宾。”这正符合儒家所提倡的“温、良、恭、俭、让”之美德, 而临战时的气度又是道家《逍遥游》中物我一如,博大无垠精神境界 的升华。习拳者如达于此境,自然正气浩然,天人合一,使身心获得 最大的放松和解放。将拳技发挥得淋漓尽至,自然会无往不胜。拳法 动作也会轻灵超脱,潇洒自如。正如识者所言,苓斋先生深谙书法之 妙,把书法中的韵律节奏之美和“轻如蝉翼,重若崩云,导之则泉注, 顿之则山安”的法则融入拳法之中,使试力松紧互为,体查身体各部 分细胞、筋络、肌腱高低、远近及冷弹惊抖等使敌莫测端倪之妙。这 就使拳学中的精神境界达到了诗情画意,律动神韵之更深的境域。
我们可以从苓斋先生的诗作中体会一下他的博大胸怀和气壮山河、 豪气如虹的气概:“拳法别开面目新,筋藏劲力骨存神,静如雾豹横空 立,动似蛟腾挟浪奔,气似长虹犹贯日,欲将大地腹中吞,风云叱咤 龙蛇变,电掣雷轰天处闻,吐纳灵源仓宇宙,胸融万物转乾坤,不知 吾道千年后,参透禅关有几人? ”
苔斋先生曾云:“见性明理后,反向身外寻,莫被理法拘,更勿终 学人。”清代郑板桥先生也有名句,道是:“四十年来画竹枝,画到生 时显熟时。”郑氏堪称画竹巨匠,弱冠之年即以善画竹而闻名,但他在 苦心研讨了四十多年后,才突然明白自己所画皆为竹之外形,乃“眼 中之竹”,于是他便削尽了冗繁而得到竹的清瘦高节的神髓,开始画 “胸中之竹”。由此,我们可以从板桥先生的画竹经历中悟出拳学之理 来。
苓斋先生在同国画大师李苦禅先生品画谈拳时,曾留下二十余副 高雅的对联,这在书画界、武林界一直传为佳话。如:“形无形,意无 意,发拳之中是真意”;“章不章,法不法,挥笔之际见真法”;“意即 无形拳,拳为有形意”;“诗是无形画,画乃有形诗”;“武至文得上乘, 画至书为极则”等(见1987年春风文艺出版社《李苦禅传》,李向明 著)。当时釜斋先生在品评画中意境时曾说:“画家之作可分为逸品、 妙品、神品、能品和俗品。远超于物象之外,意趣超迈,出神入化之 作称为逸品;有独特意境,可以论神韵;不可以求形器之作称为妙品; 神品是指那些风格新颖,技法独到之作;至于能品与俗品之作只能以 外形酷似为能事,而不能谓之意匠”。
苔斋先生当时就根据画中意境告诫在场众弟子:“习拳应只求神意 足,莫求形骸似,要努力在意境方面求索,应成拳学意匠。”可以说, 没有竭尽全部精力至殉道精神是不易达到意匠境界的。
当然,有了这样纯净高远的精神境界不但“万物静观皆自得”,能 专心体会操练拳法之妙,而且再不会感到烦累难支和枯燥无味,站桩 过程也不再会成为负担,反而会觉得是一种净化心灵、陶冶情操的莫 大享受。
苔斋先生自幼聪慧过人。形意拳大师郭云深在未见到他时,就听 说他在同塾师谈论一直被文坛推崇备至的王勃名作《滕王阁序》时, 竟指出“落霞与孤鹫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两句,乃是仿照庚信 《马射赋》中“落花与芝盖齐飞,杨柳共春旗一色”而成。当时郭老就 对年仅八岁的英斋先生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和好感。只因芸斋先生体弱 多病,才开始习武健身。
弘一法师是我国近代著名的佛学大师,他不仅精通文字、书画艺 术,而且对戏剧和音乐亦有很高的造诣,他饰演黄天霸的英姿,至今 为梨园所乐道。他创作的《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至今还广为传唱。苓斋先生在游 历江南时专程去西子湖的虎跑寺拜望他,故而在佛学和书画方面得到 了极大的教益,二人相交甚厚。
从某种意义上讲,二人大彻大悟的灵犀是相同的,只是法师是在 参透禅关后才循入空门,而苔斋先生则是在花开佛现后毅然留在了 “苦海”。先哲曾言:“人最苦的事莫过于苦于身上背着一种未来的责 任诚哉斯言!
其实,每个人的拳学造诣都会反映出他的品德、情操、学问、阅 历和精神境界的深度。由于人品和学识及对自然界的感受不尽相同, 而反映的精神境界也必更异。习拳者要达到高远的拳学境界是件极不 容易的事,正如弘一法师书赠警斋先生的诗句所云:“痛感世事洒血 泪,深受楷模动魂灵;迭患沧桑心方觉,万卷书破理渐通”。
当王苔斋在创立新拳学后又去探望弘一法师时,法师有感他“穷 苦艰危独自撑“和“万言谤诽衣带宽,妙悟禅关集大成“的松竹节操, 当即挥毫题诗相赠,希望习练拳学的同道,能从诗中领悟到事业的艰 辛和成功的“秘籍”。
习拳除苦练拳法外,还应有文化和道德上的修养。
王国维是近代著名的国学大师,他多年矢志不渝地埋头研究商周 历史、地理,边疆少数民族史,古代碑刻、音乐、音韵、文字、古籍 考证,以及有关经学,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尤其是殷的历史,孔子 曾经发出了三代文献不足的感叹。晚于孔子四百多年的史学家司马迁 在选写商殷的历史时也因文献不足出现了可以理解的一些差错,这些 差错却被两千年后的王国维纠正了,所以历史学家郭沫若说:“殷墟的 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的开始”。
王国维的重要著作《观堂集林》在他死后的第二年被正在日本从 事历史学研究的郭沫若发现了。郭氏认真阅读后,赞叹说:“《观堂集 林》和它的作者在史学上的划时代成就使我震惊了”。
王国维是个很有反思气质的思想家,他深刻意识到中国传统思维 方式“除迫于实际之需要外,殆不欲穷究之也”的急功近利的实用倾 向,功利性造成“我国学术尚未达自觉之地位”的客观结果以及文化 总也摆脱不了作为政治工具的命运。
王国维说:“夫然故,我国无纯粹之哲学,其最完备者唯道德哲学 与政治哲学耳。至于周秦两宋间之形而上学,不过欲固道德哲学之根 柢,其对形而上学非有固有之兴味也……抑亦哲学家美术家自忘其神 圣之位置与独立之价值,而芯然以听命于众故也”。
在王国维看来,哲学与美术实乃天下最神圣、最尊贵但却“无与 于当世之用者”。这是因为“夫哲学与美术之所志者,真理也。真理 者,天下万世之真理,而非一时之真理也。其有发明此真理(哲学 家),或以记号表之(美术)者,天下万世之功绩,而非一时之功绩 也”。
他还在中国历史上破天荒地提出:“学术之所争,只有是非真伪之 别耳。于是非真伪之别外,而以国家、人种、宗教之见来之,则以学 术为一手段,而非以为一目的也。未有不视学术为一目的而能发达者, 学术之发达存乎其独立而已”。
王国维对哲学、美术独立价值和神圣地位的确认与肯定,对传统 文化“以政治及社会之兴味为兴味,而不顾真理之如何”的功利主义 价值观的冷峻批判,究其实并不是要为哲学与美术在传统文化的格局 中争得一席之地,而是在近代中国中西方文化激烈碰撞、传统文化不 得不开始现代转型的历史背景上,对民族文化究竟如何发展的一种根 本思考。
苔斋先生在文学方面颇多受益于王国维。二人相识于1922年,当 时王国维在北大任通信导师,二人结交后经常彻夜长谈。一次苔斋先 生谈起了拳学意境,王国维当即把他在《人间词话》中对成大事业、 大学者的追求所提出的三个境界书成条幅,请人装裱后赠给苓斋先生。 要斋先生认真品味后频频颔首,将条幅悬于正屋壁上,并时常向弟子 们讲解其中含义,可见他对王国维的提法是很赞同的。
王国维提出的三个意境是他寓以新意的三位宋代词人的名句。第 一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词句出自 晏殊的《蝶恋花》,原意是说,“我”上高楼眺望所见的更为萧飒的秋 景,西风黄叶,山阔水长,案书何达?在王国维此句中解成,做学问 成大事业者,首先要有执着的追求,登高望远,瞰察路径,明确目标 与方向,了解事物的概貌。
第二种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引用的是北 宋柳永《蝶恋花》最后两句词,原词是表现作者对爱的艰辛和爱的无 悔。若把“伊”字理解为词人所追求的理想和毕生从事的事业,亦无 不可。王国维则别有用心,以此两句来比喻成大事业、大学问者,不 是轻而易举,随便可得的,必须坚定不移,经过一番辛勤劳动,废寝 忘食,孜孜以求,直到人瘦带宽也不后悔。
第三种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 处。”是引用南宋辛弃疾《青玉案》词中的最后四句。这是借词喻事, 与文学赏析已无交涉。王国维已先自表明,“吾人可以无劳纠葛”。他 以《青玉案》最后四句为人生智慧最终最高境界。这虽不是辛弃疾的 原意,但也可以引出悠悠的远意,做学问、成大事业者,要达到第三 境界,必须有专注的精神,反复追寻、研究,下足功夫,自然会豁然 贯通,有所发现,有所发明,就能够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
后来,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一文中,又把这三境界说成“三种 之阶级”。并说:“未有不阅第一第二阶级而能遽跻第三阶级者,文学 亦然,此有文学上之天才者,所以又需莫大之修养也”。
古往今来,追求拳学真谛者多如牛毛,但成功者却如凤毛麟角, 究其原因虽多,但主要是意志不坚,恒心不足,境界不高所至,或见 异而思迁,或始勤而终惰,虽偶有所得,不过庸中佼佼而已(见杨鸿 尘撰著的《王苔斋拳学》,河北科技出版社1993年版)。
(3)
20世纪40年代,苔斋先生在答记者问时就说过:“要知拳学乃人 之需要,不可须臾离一贯之学也。故庄子说:技也进乎道矣,诚文化 艺术之基础,禅学哲理之命脉,若仅以此微效而可以代表拳术,则拳 学当无考究之必要矣。”
在与苔斋先生同时代的识者看来:“大成拳,平易近人,老幼习之, 均易于收效。弱者可以强,病者可以愈,即含有慈的意义。为子女者 习之,可免父母之忧;为父母者习之,可慰子女之心。学问家及有用 人物习之,对于学业进步及事业整理,均有莫大裨益。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吾人抱儒家泛爱众而亲仁之意义及颜李学实践精神, 以推广大成拳于社会而普及于人群,则是人类健康保障及和平气象, 必能洋溢于世界。”
我以为,习练大成拳者,不见得都能或都应该成为技击高手,但 只要你能坚持练下去(尤其是在桩功上),就一定会对你的身心、事业 和情操大有益处。
如能由拳学而进入国学成为学养深厚的学者,则是人生一大幸事 也。同时,这也是提高国民素质的有力措施之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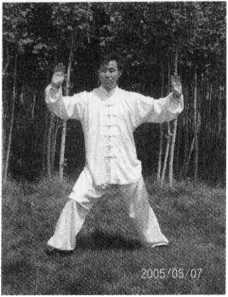

浏览1,708次